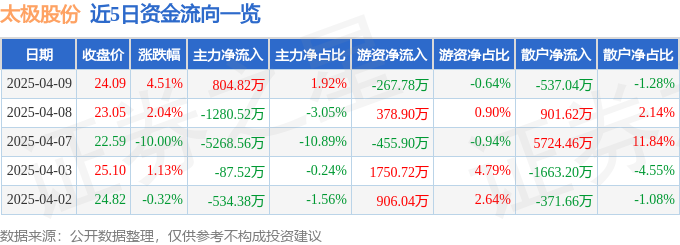口述保险史⑦丨王恩韶保险70年:总理保住了行业,还说保险立了功

口述丨王恩韶 采写丨徐晓
编者按
本期人物:王恩韶,1922年1月27日出生,2015年10月19日逝世,享年93岁。
他的故事,可从其父亲王伯衡讲起,乃中国保险史上的知名人物,1929年参与创立太平保险公司,曾任第二协理。
这或许注定了王恩韶与保险的缘分。他年少时考入上海东吴大学经济系,20岁毕业进入保险直至退休。
解放前,他先后服务大上海分保集团、太平洋保险(601601)公司;解放后,他进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那个年代的保险高知,也是为数不多的常年与海外业务打交道者。
如他曾长期担任人保公司国外业务部再保险科科长,经手处理了“跃进”轮沉没等一系列重大赔案,并两赴越南建立保险公司;
也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处处长、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中国执董办公室顾问、副执行董事,人保驻伦敦联络处首席代表,中国保险公司(英国)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
1991年退休回国后,还曾被刚从人保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的秦道夫钦点为保险法起草组副组长,组长是秦本人。
之后,他悉心培养保险新人,受邀担任多所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不仅成立“保险清寒同学奖学金”,资助贫困学子,还身体力行关注平安、泰康等市场化险企的成长,出任高级顾问。
纵观王老的保险70年,不仅为行业奉献了一生,更参与见证了中国保险业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恰如一部中国保险史的缩影。
而《口述中国保险史》的推出,恰是为了“挖掘”这些即将甄灭的记忆,讲述一代代中国保险人的故事,续接一个行业。
本期推文,是纪念,也是回望。

我从1942年大学毕业就干保险,经历了旧中国半殖民主义色彩的保险业和新中国保险业曲折发展的各个阶段。
解放前夕,中国保险市场主要由四个官僚资本保险公司所垄断,它们是:
中央信托局保险处、中国银行(601988)的中国保险公司、交通银行(601328)的太平洋(601099)保险公司、中国农民银行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华商民营公司如太平、大安等共有一二百家,业务越来越小。
那个时候的中国再保险业却是由西方国家垄断的,每个保险公司的分保都给国外。当时因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很小,更没有自己的船舶,寿险保额又很低,所以分出的业务主要是火险业务(即现在的财产保险)。分出分保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伦敦市场,二是瑞士再保险公司。另外还有一个是美国,特别是美亚保险公司(AIU),抗战胜利后卷土重来,狠捞了一笔分保费。
前面讲到的四个官僚资本保险公司的业务累积责任比较大,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外分保。
一种是固定分保合同,主要给伦敦市场、瑞士再、美国公司,合同定有自留额。1948年~1949年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飞涨,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发工资要带着枕头套去公司装钞票,拿到工资马上到马路上去买银圆,凑够了银圆再去换“小黄鱼”(金条)。通货膨胀对分保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公司分出分保合同中的自留额均以伪法币为分保货币,在1945年~1946年最初订定合同时,根据伪中央银行订定的汇价,一美元等于伪法币四元,5000元伪法币自留额相当于1000多美元;而贬值之后,市场上按黑市汇价折合美元的款额越来越少,以致于最后自留额基本上是形同虚设,这就意味着分保的需要越来越大。
第二种分保方式,即临时分保,主要是分给当时在上海营业的外国保险公司。由于外国保险公司资金实力较强,分保限额又是按美元或英镑等外币计算的,又有各公司的总公司后台的支持,接受分保的金额比较高。因此,当时我国的财产保险业务,90%或更多是通过分保方式分给了外国保险公司(人身险业务由于当时货币贬值,很少有人问津,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当时的另一个特殊情况是保险赔款很少。因为物价飞涨,商人都把货囤积在仓库里不想卖,对财产的看护就特别在意,出险率很低。所以,保险公司分出去的都是好业务,利润率特别高。
还有一个因素:我们付出的分保费,在黑市上不值钱,而外国公司按“央行”的官价折合成外币,合法汇出,等于又捞了一票。根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1949年我国通过分出分保流出的保险外汇高达2000万美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时期总公司设在上海的各家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但考虑到中国银行属下的中国保险公司(简称中保)与伦敦市场有二三十年的业务关系,而且在东南亚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如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和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人民政府决定保留中保,并指定专营国外业务。
1949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成立以后,人保与中保在国外业务方面有个分工:
苏新国家(苏联及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业务由人保做,西方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地区的业务由中保做。
人保成立了国外业务处,施哲明任处长,同时他也兼任中保的第一副总经理。事实上,中保是由人保国外处领导的。
1951年,中保由上海迁至北京,在南长街办公。
那时候,国外业务仅办有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保也就成为专业的进出口货物保险公司。中保的对外分保主要通过伦敦的保险经纪人公司Willis Faber & Dumas安排,只有分出,根本没有分入。
同时,中保还保留了当时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内办公的一名代表,是英国人,名叫 Noble,负责跟英国市场打交道。
刚解放时,中国一面倒学苏联。有一本书叫《苏联国家保险》,讲到国家的后备有三种,一是财政,二是自留后备,三就是保险了。这话说起来没什么错,但执行起来往往就偏了。
1949年9月2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人保公司成立事宜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国家可以减少大量之建设财政开支……亦为平衡预算收支之重要保证。
当年9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第一届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确定保险的基本任务为:“保障生产,促进物资交流,保护国家财产,并提高劳动人民福利。”
这个基本任务阐述得还比较侧重于保险的保障作用,但从中央的思路中,更重视的是财政预算手段,因此保险运作起来,自然而然地就会偏向于此。
建国初期,保险公司的主管单位换过好几次,最初是由财政部领导,后来是由人民银行领导,后来又划到财政部。
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保险的保障功能不完全了解,导致这种轮换。张蓬本来是上海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就任保险公司总经理,有一次他调研回来以后说:
我认为保险不是火腿肉,连包火腿肉的纸都算不上,只能算是捆火腿肉的绳子。这意思是说,虽然保险多少也沾点油水,但微乎其微,对财政的贡献很少。

所以,那时候做保险也容易也不容易:
容易,是指你对保险保障这块功能的发挥用不着更多考量;不容易,是指保险费收入实在有限,钱上不来。
由于保险被视为财政或人民银行长期累积资金的工具,上缴金额又相对较少,所以大家认为保险不是块肥肉。也因为这个特点,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不是十分重视,因此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在内部设立管理保险的专职部门。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仅有一家保险公司,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当时也没有什么监管条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己定了一个保险管理规定,就是总公司用来管分公司。对于外国人来说,这就不大好理解。
1959年,我们到开罗开FAIR(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会,林震峰副总经理作为人保公司的代表,我作为业务人员兼翻译跟着去。头一天开业务会,他出席参加,而且介绍了中国的保险业务情况;过两天开保险监管会,他又参加了。
别人感到奇怪,于是当时埃及一位再保险公司总经理说:“我们开业务会你参加,我们开监管会你又参加。业务是被监管的,监管是要监管业务的,你一人又是业务又是监管,你是在用左手管右手,管得了管不了?”这话既是笑话也是正经话,因为他不理解啊。当时,林震峰副总经理也没法多说,反正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回来以后就向上级汇报。
第二年又开会,就加派了李聘周,也是人民银行的人,以监管身份参加监管会。林震峰也去,参加业务会。翻译不多带,还是我去,我就跟着林震峰跑。李聘周那儿没人陪着,光杆司令,别人想跟他了解监管,他不懂外语,也没法子跟别人沟通。其实这是我们一个策略,别人就感觉中国人做事儿都是很奇怪的。
所以讲到保险,不仅是老百姓(603883)不清楚,做保险的人、领导保险的人对保险的作用、办保险的目的,很多都不是从保险的保障角度来考虑的。

1965年,越南财政部陶副部长向王恩韶颁奖
到“文革”时期,残存的这一点保险也差点完了。
1966年3月21日到4月7日(不知为什么当时开会时间都很长),人行在京召开全国外汇、侨汇工作会议,会议在高涨的政治气氛中召开,会议提出:
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贯彻执行一条方针、两个服务、三个观点和四句行动口号,即: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外贸和华侨两个服务,政治、生产和群众三个观点,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怕苦和四不怕死的四个口号。
从这些词句,就能感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在文革中,一些人指责人寿保险是活命哲学,财产保险是封资修的产物,办保险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保险公司是剥削公司,必砸烂而后快。
具体到分保业务也有说辞:即使赚了外国人的钱也是参加剥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符合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如果赔了钱就更不得了――那不是帮着外国资本家赚中国工人的血汗吗?
当时军代表进驻金融单位,来了以后就听汇报。那时候保险公司属于人民银行领导,他听完人民银行各个司局汇报后,总结道:
今天大家汇报,信贷局、储蓄局啊等等,我都听明白了,只有保险我听了半天,不理解。因此我给保险下个定义,什么是保险呢,叫“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这是在大会上讲的。
后来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一起组成人民银行下属的国外业务局,这样保险就降为处级单位。全国的机构只有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人员只有百八十人。
1969年北京的保险总公司干部下放,只留下9个根正苗红的人收拾摊子,我们这些人收拾行李下去,就没想着还能回来。谁知我下去没三个月就回来。
当时中国惟一的还在开展对外贸易联络、展销、对外交流和法律仲裁等事务工作的机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他们工作中有许多问题涉及到保险,比如共同海损,找那留下来的9个人,太难为人家了,于是借调我回来,并明确告诉我,“当个拐棍使使”。
在国际上,只有一个《安特卫普理算规则》,我们就自己搞了一个《北京理算规则》,还真结了几桩案子,那时就是想把付给外国海损理算资本家的钱抓回来。
我被借调回来当拐棍,说明保险还是有用的,但后来我还是回到干校去“补课”了,说是锻炼得不够。
但因为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使保险残留下来的一点血脉得以延缓。一是中国民航替柬埔寨运送的铂金被盗,二是印度驻华使馆的车子出了车祸。这两件事都打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这才知道保险要被撤了,保险这才保存下来。

1993年,保险法起草小组访问柏林。
1963年4月,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海轮“跃进”号装载1万多吨玉米,从青岛出发首航日本门司港。4月30日开出,第二天在经过南朝鲜海域时就触礁沉没了。当时我国还未与日本建交,日本华侨、进步人士在门司港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准备迎接“跃进”轮的到来,没想到却等来了这么个坏消息。
“跃进”轮是有保险的。
从1956年8月1日起,中保在国内停止经营,全部业务包括分保业务都转由人保办理。人保的国外业务处下设三个科,分别是业务科、再保科、海外科。再保科由我负责,其下合同组共有张鉴、李嘉华、周庆瑞、韦向辰等四人,“跃进”轮的分保就是再保科办理的。
我记得“跃进”轮保额120余万英镑,我们自留20万,其余100万主要是通过Willis在伦敦市场分保。我们是在“跃进”轮出航前的那个星期通知Willis办理分保的。Willis接到分保电传后,就拿着分保书在劳合社开始安排分保,各个承保人(underwriter)接受了就写个数字签个名。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条船,大家考虑的时间都较长,启航之前总共分出了80万英镑。
5月初的一个周末,我们几个人正在张鉴家里打桥牌,上午10点钟,施哲明处长“咚咚咚”敲门进来说:“糟糕了,跃进轮沉掉了!”这下大家都很着急,马上开始商量该怎么办。主要有两个顾虑:第一,虽然伦敦方面发来电传,告知已经安排了80万英镑的分保,但并没有出保单,会不会赖帐?第二,我们要求分保100万,才分出80万,那20万算不算数?几个人整整商量了一下午。
第二天上班后,我们即给Willis发电传说:关于“跃进”轮分保事宜,相信你方已全部安排完毕,请出具保单。
对方回电道:我方收到分保申请后即去劳合社安排,因时间所限,只分出80万英镑,并已通知你方,这80万英镑没有问题。本当继续安排所余20万英镑的分保,但日前我方一进劳合社,劳合社的“卢丁”钟就响了,报告了沉船的坏消息。所以非常抱歉,20万英镑未能再行分保。(注:“卢丁”钟是一艘名叫“卢丁”的沉船上的船钟,悬挂在劳合社的承保大厅。遇有船舶失踪、沉没等重大事故,就敲起这个船钟,提醒承保人不再接受该失事船舶的业务)
由于这是中国自建的第一艘万吨轮,也是人保出具的第一份海轮保险单,很多技术问题都需要逐一核实清楚,所以出单比较晚,但能分出80万英镑已是不幸中的大幸。
对于沉船的原因,我国政府怀疑有两种可能:一是触礁,二是美帝破坏。
经过了解,船舶持有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在工作安排上比较仓促忙乱,例如:船长对船的性能、要经过的海域情况都比较生疏;选择的路线也是个问题,由于敌情观念太强,有意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以避免美帝潜艇的破坏。这些情况虽不影响我们立案和承担赔偿责任,但也极易被分保接受人找茬赖赔。
“跃进”轮事件在当时很轰动。周恩来总理亲自对此事一抓到底。
5月中旬的一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要我们领导带一名业务干部马上到国务院去。领导是人保的林震峰副总经理,业务干部就落到我头上。
临走,施哲明处长叮嘱我:“老王,业务问题要向领导解释清楚,把所有的资料、条款、保单、海上保险书都带去。”那时候还没有塑料袋,我就用一个布袋装了这些资料,跟林震峰副总经理去了中南海怀仁堂。进门以后,我把布袋放在了座位底下。
总理说:船虽然沉了,但我们有保险,能不能从国外拿回赔款?交通部说可以拿回80万英镑。保险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简要汇报了分保情况,介绍了分保接受人的义务。
总理问:外国保险公司赔不赔?
我们答:赔。
总理问:条款怎么定的?
我们解释道:责任范围包括触礁、搁浅等海上风险。
总理问:如果是被潜艇打沉的赔不赔?
我们说:赔,那属于战争险。
总理又问:如果是被直接打沉的赔不赔?
我们说:那更应该赔了,那就是战争险。
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的除了交通部、外交部等部领导外,还有一些解放军的领导,对于西方保险不很熟悉,听了我们的话,有位高个子的老将军(外号“罗长子”的罗瑞卿将军)一拍桌子说:如果是美帝国主义打沉的话还能赔钱?像是不相信。
我们就介绍道:我们这是两种险,一个是Marine Risk(航运险),一个是War Risk(战争险),如果触礁我们赔,如果是美国打沉的,我们也赔。
罗瑞卿又说道: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哦!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
周总理显得比较高兴,嘱咐说:好,保险公司抓紧对外索赔,这些情况你们向外交部汇报,请外交部条法司的专家帮助研究一下,争取早日要回赔款。
这次汇报前后也就10分钟左右。我起身要走时才发现座位底下的包不见了,“我的包呢?”我情不自禁问了一句,有人把包递还给了我。原来是总理身边的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把布袋拿走,放在他们身边,而我因只顾紧张,都没发现。
“跃进”轮的保险赔付还是不错的,除了劳合社之外,我们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业务往来,它们也接受了一些分保,后来赔款陆陆续续都摊回来了,总共104万英镑。
据说,总理在总结的时候说:“跃进”轮沉没,船长有问题,其他相关部门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有保险公司立了功。“跃进”轮事件,我们在经济上没有损失,但是在政治上有损失。
这事儿我们保险公司也感到挺自豪。
跃进轮的120万英镑保额是比较高的。据交通部经办保险事务的赵仁隶事后告诉说,之所以这么高,一是因为国内的造价比较高,二是此船是按苏联巡洋舰的规格造的,钢板的标准比普通商轮高。
我们办理分保的时候,Willis也问过这问题,说是国际上都没有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回答说:水险保单是定值保单,我们跟投保人交通部确定的保险价值是120万英镑,并按120万英镑足额承保,分保也按这个价值办理,并无不妥。
据说这个金额可以在西方船舶市场购买两艘同样水平的船。
再保工作的政策性和技术性都很强,要做到既不崇洋媚外,又不贬洋排外,但我们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还是克服困难,作出了一些贡献。
有几点值得说一说。
中国独立自主地摆脱了西方国家的垄断控制,制定了自己的再保方针政策。表现在分出分保合同上,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取消了经纪人条款。过去分出分保合同规定,安排分保合同接受人、支付保费和摊回保费、赔款,什么事都要通过Willis办理,我们和分保接受公司之间不见面,业务实际上被经纪人操纵了。经过一步步地说理斗争,最后我们把这一条给取消了。
二是修改了仲裁条款。按照国际习惯做法,分保合同人间发生争议,仲裁地点一般都订明在分出公司所在国进行,使用该国的仲裁规定,或者在既非分出国又非分入国的第三国进行。但过去,中保等公司的分出合同都规定,争议必须交由英国商会或海事委员会仲裁处理,岂不是很不合理?我们经过交涉,争取到将仲裁地点和单位改为在北京由中国贸促会仲裁委员会处理,维护了民族自尊。
三是加大了我方处理赔款的权利。过去损失达到一定额度以上的,必须先经由分保接受人审核同意,我们才能支付赔款,发言权完全掌握在分入公司手里。后来改成不论赔款金额多高,均由我们全权处理,分保接受人必须接受。
四是提高了自留额、分保手续费率和纯益手续费率。过去我们的自留额很低,只有2000~5000美元,与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完全不相称,每笔业务都要分出50%~90%给外国公司,我们等于给他们作了代理人。
经过很多回合的较量,我们的自留额逐步提高到20万英镑,这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比较高的。分保手续费率也由过去的15%~25%提高到37.5%,纯益手续费率由10%~20%改为30%~40%,并用累进方式计算。如此之高的手续费率在当时国际保险市场上是罕见的,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合同质量好,是赚钱的。
但在解放前,即使赚钱的业务也很难提高手续费率。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的合同内容已经与国际市场相吻合,不合理的条款被完全取消了,再保险业务的发展比较平稳。
特别是开展了分回业务,强调对等分保:分给谁10万美元业务,也要想办法从他那儿接受别的合同,分回10万美元,条件对等,保费也对等。每年初续转合同的时候,都要把这项工作做一遍,分回业务成份不断提高。

建国后,我们因为跟劳合社有业务关系,就在伦敦设立了个机构,叫人保驻伦敦联络处,专门做联络工作,这大概是1955、1956年的事儿。名为“联络处”,其实联络工作并不多,往往是国内需要巨额分保的时候才会找到联络处去办。
后来人保就和中国银行商量,两家出资在伦敦设立了中国保险(英国)有限公司(简称英中保),并于1985年10月1日签发了第一份保单。
我是1985年8月去的伦敦,出任人保驻伦敦联络处首席代表、中国保险(英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英中保规模并不大,每年的保费收入也就是一两百万英镑。可我们在伦敦有一件事儿是做对了,就是没有接受责任保险。当时在国际市场上,责任保险是一种新的业务,在美国特别吃得开,英国伦敦劳合社当时也在逐步地开展着。
我们当时对责任保险具体情况不了解,国内也没有,所以就决定先看看再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责任保险保费是很多,可是赔款更不得了,主要有两项,一个是石棉污染责任,还有一个是雇主责任。
尤其是石棉污染责任,房子刚一盖好的时候看不出来,但是石棉本身有问题的话,以后的赔款就理不清了,而且是个“长尾巴”责任,美国很多保险公司就是因为石棉保险赔了钱,关了门。后来又发展到经理人责任保险,这也是一个扯不清的官司。
英中保没保责任险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些“责任”不好理解;二是我们在技术上也不熟悉。就缓了缓,一看前景不好,英中保就始终没有接受责任险业务,这件事做对了。
所以,英中保虽然保费收入数字不大,但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也是在当时英国保险市场上为数不多能够赚钱的保险公司之一,因为大多数公司都是在做这个责任险。
1991年5月,我退休回国。
1991年,王恩韶离任英国时同事合影
(本文采写于2014年)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今日保。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